胡景耀2021年6月在国家天文台接受《赛先生》采访,摄影:辛玲
【编者按】
曾有人将胡景耀誉为中国光学天文的开拓者:第一位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的中国本土天文学家,改造60厘米望远镜并发现了我国第一颗河外超新星……而于他自己而言,却更喜欢“天文老顽童”,说话、行事的风格其实就可见一斑。2021年6月,胡景耀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接受了赛先生天文的采访,我们将胡先生口述的人生经历及对未来中国光学天文观测的看法整理、编辑成文,以飨读者。
口述 | 胡景耀
采访、整理 | 辛玲
责编 | 韩越扬、吕浩然
- 抽签抽到南大天文
我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我们一共五个孩子,父亲在宁波火柴厂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家里还有地,出租给农民。我记得有次跟妈妈划着船去收租,农民给多少稻子都行,因为家里其实不愁吃穿。我大哥高中没毕业就被舅舅拉去当新四军了,参加了四明山游击队。我们家的家风一直比较开放。
我中学的第一年是在宁波效实中学念的,我最近发现屠呦呦是我的校友。后来转到杭州高级中学。我是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整天喜欢玩。比如上课讲到达尔文和嫁接,我就和同学试着让一株植物下面长土豆,上面长西红柿。结果,还真的长出来了。后来我们又做炸药(编者注:口述彼时的经历,请读者勿做现已违法的行为),也做成了。总之我那时很调皮,考试成绩不怎么好,也没做过跟天文特别相关的事。
后来为什么考天文系呢?因为大学天文系招的人少,我觉得竞争肯定不那么激烈。当时我有个要好的同班同学,叫王一鹏,念书比我好。我起初想上北大物理系,可是北大物理系一共也招不了几个人,我和王一鹏岂不是要碰头?还有什么可考呢?要不就南京大学天文系吧。南大天文系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天文系,是中山大学和齐鲁大学的天文系在院系调整时合并而成的。那时的大学录取名单是在报纸上公布的,我看到上一届一共也就录取了30来人。
至于我和王一鹏谁考北大物理系、谁考南大天文系,是通过抽签决定的(先抽签决定考哪里,再考试)。结果我抽到了天文系。他到北大物理系后学习很用功,但因为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说了一句无心的话,被打成右派。我这人喜欢到处说,在南大却平安无事。
在南大天文系的学习相对较苦:数学课跟着数学系一块上,物理课跟着物理系一块上,但却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时的观测,国内基本还在用经纬仪。紫金山天文台60公分的望远镜刚刚修好,是国内口径最大的,很稀罕,那时还轮不到我们用。
- 从河北兴隆到美国德州
我是1958年从南大天文系毕业的。毕业前一年的夏天,程茂兰先生从法国回来,开始引导天体物理成为中国天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当时,主管部门同意在北京新建一个天文台,办公地点就在中关村微生物所的三楼。同时,还要建一个观测站。我就参与到了观测站的选址工作中。
由于选址需要一个能测大气扰动的设备,我就去了当时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上海天文台,在那里呆了半年,做了一台记录星光闪烁的仪器。然后拿回北京来用,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北京天文台的一员。
选址时,晴天数多是很关键的。华北和西北的晴天数都比较多,选在北京附近有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程茂兰先生提出,天文台的观测工作和科研工作要适得其所,观测应在山区、大气平稳的地方,而科研工作和天文台的大本营应该设在城市内部,方便大家交流。当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觉得干嘛非跑那么远去观测,像紫金山天文台(在南京市内)那样就行了。
到了1977年,美国来了个天文代表团。那个代表团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主要天文台的台长。其中,德州大学麦克唐纳天文台的哈伦·史密斯(Harlan J. Smith)跟我们聊得很好,邀请我去他那里访问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德州我做天文设备和观测,还买了一台计算机带回国。
等我从德州大学回国继续选址工作时,我就对近代天文台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了一个基本概念。我特别认同程茂兰先生的观点,他对中国观测天文立了大功,在国外积累了很多经验,很清楚应该怎么进行天文观测。他带着我们选址,去太行山从南跑到北,又去燕山从东跑到西,最后选了兴隆这个地方。
由中科院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北京天文台和自动化研究所联合研制的2.16米光学天文望远镜于1996年12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通过了由中科院主持的鉴定
- 寻找行星和超新星
到了1981年,又来了一些荷兰天文学家。我们相谈甚欢,他们又邀请我去荷兰访问。因为家庭和孩子年幼的原因,我就半年在荷兰、半年在国内工作。荷兰是欧洲南方天文台的成员国,所以那期间我还去智利观测了三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欧南台在智利的所有望远镜我都用过,小到40厘米、大到3.6米,还有16米的亚毫米波望远镜等。我挨个申请了观测时间,把它们的性能了解了个遍。有一次,我一晚不落地观测,连着观测了一个月,到后来实在没有力气了。天文台的大夫通过广播向大家求助,说有个“胡”快不行了,这下整个天文台的人都知道我病了。
当时我主要是利用光学和红外波段的光谱分布寻找行星系统。比如说,一个恒星本身的光谱曲线和温度是确定的。如果在它的光谱里面出现了一个小凸起,那就说明在它周围有比它“冷”的东西,可能就是行星系统或者是行星形成之前的碎片。我就找了一批这样的东西,做了样本。
随着我的海外访问行程告一段落,北京天文台希望我接管北京天文台兴隆站的管理工作,因为当时的站长身体不太好。管兴隆站也挺好玩的。还经历了几次媒体高潮:一次是流星雨,一次是海尔-波普彗星过境。那时,仿佛所有的记者都跑到兴隆去了!
这段时间里我的研究兴趣是找超新星,这是在欧洲就定下的方向。在欧洲时,我没事就在图书馆里乱翻,意识到超新星很稀罕,它们是偶然出现的,找到之后进行后续观测很重要。我在欧洲做了些准备工作。回国后,兴隆站那台60厘米的望远镜是闲置的,我就想办法改造它。它原来是卡塞格林系统,我就把后面的部分去掉,在主焦点上加一面改正镜,视场扩大到1度左右,可以看到好多星系和星系里的超新星。
除了主镜,还需要一部CCD相机(电荷耦合器件相机,一类老式数码相机),我就从认识人那里花5000块钱买了一个,装上了。利用这个改造的望远镜,我们拍了很多星系的照片,然后比对随时间的变化,噼里啪啦找到了一堆超新星。兴隆还成了全世界找超新星最多的天文台之一!超新星研究在当时还不是很热门。找到超新星以后,坐落在不远处的2.16米望远镜就可以跟踪观测更多的细节了。
- 把望远镜放到月球和南极
到了嫦娥三号,我们国家要往月亮上放东西。放什么呢?我就想那里既没有云、又不会下雨,放个望远镜上去不就行了吗?!一般来说望远镜有个麻烦,就是它要跟踪天体。但在月亮上的望远镜不用动,随着月球自转就会扫过一片很大的天区,每过一段时间还能循环观测。而且这个望远镜要弄得越“傻”越好——越“傻”越可靠。
最终,一台15厘米的紫外光学望远镜顺利登上了月球,这台望远镜一直运行得很好。从2013年底落到月球上开始,它远远超过了设计寿命。
关于南极望远镜,好像是在香山开会的时候,有人问我对南极天文观测有什么建议。我就想:南极有小半年是全黑的,而且南极点在天空的位置也基本不变,可以在那里长期监测一些天体。我就建议做四个施密特望远镜,口径不要大,但视场要大,在四个不同的波段对目标天体进行观测。名字可以叫CSTAR,the Chinese Small Telescope ARray(中国小型望远镜列阵)。设计望远镜的时候,我就坚持不要弄得很复杂。那个地方没有人长期驻守,咱们就立几个望远镜在那儿,能把数据传回来就好了。
- 光学天文未来之路
应该说郭守敬望远镜LAMOST是很成功的望远镜,而在LAMOST之后中国的光学天文应该做什么可以很好地讨论一下。我觉得现在一些人有点应付,抱着“没事就接着做,总有用的”这种想法,而不是去开发一个更有用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文的发展基础还是在光学波段。如果光学弄不好,其它波段要冒尖也难。
光学天文的下一步,做更大口径的望远镜肯定是主要趋势,因为接收到的光子数更多。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能够接收相同数量的光子,而设计要尽量简单”?比如十米级的望远镜,要考虑单镜面以外的技术可能性。这么大的单镜面很难,支撑系统尤其麻烦。这件事其实我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只是觉得大家应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好好讨论一下。
还有,中国光学望远镜的大本营要放在哪里?是立足国内,还是像欧洲一样放到海外?我比较悲观,我觉得以中国的气候条件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台址(编者注:采访时青海冷湖的选址工作还未最后确认)。个人想法,东非其实可能是个好地方。观测条件上,东非和智利很相似,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在国外放个大口径望远镜是一种做法。在国内的话,就不一定追求大口径,可以从时间或波段角度去考虑。
另外,中国现在空间技术发展得不错,也可以考虑放到月球上去,要在月球上放一个2米或3米的望远镜可就厉害了。要做成一件事是很难的,要综合考虑国力、技术实力,看做什么最有利,对中国天文的发展最合适。这需要一个冷静、明智的领头人来做决断,也需要集体的力量和内部团结。
注:本文整理自胡景耀先生采访口述,仅代表受访者观点。
致谢:感谢国家天文台薛随建老师对采访的大力协助,以及陈颖为老师为本文精心选择老照片。
本文地址: 转载-胡景耀:我们自己改造的望远镜,看到了我国第一颗河外超新星 | 赛先生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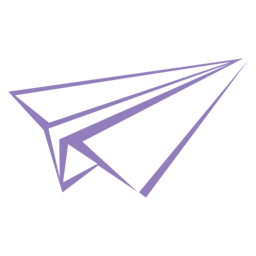
您必须 登录 才能发表评论